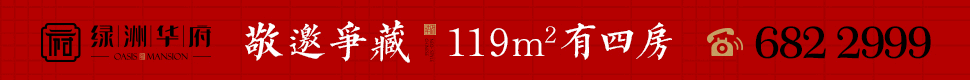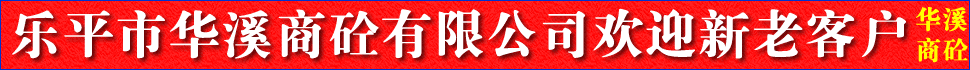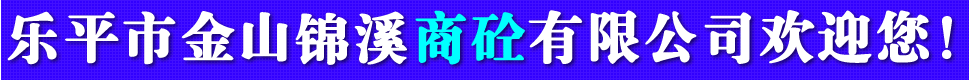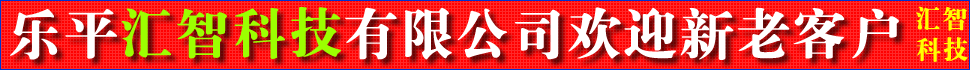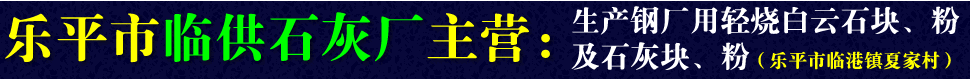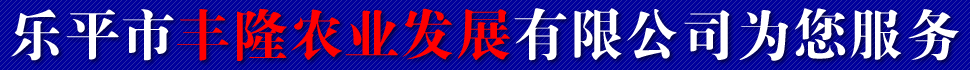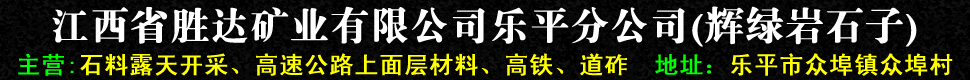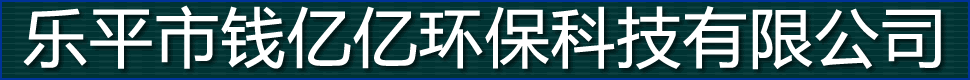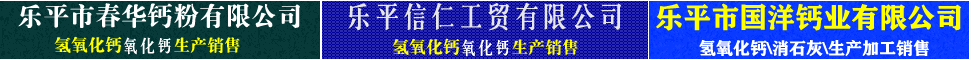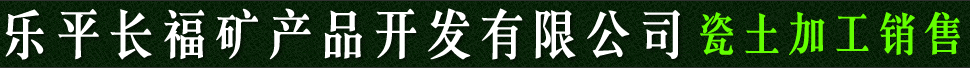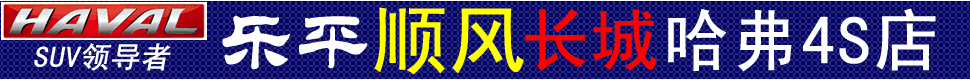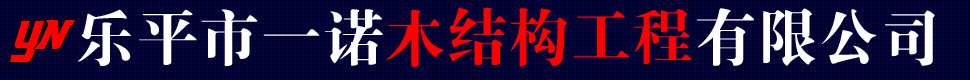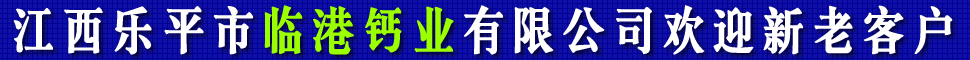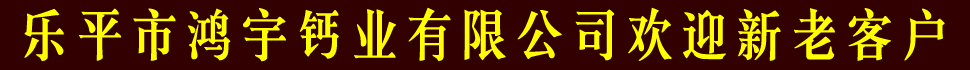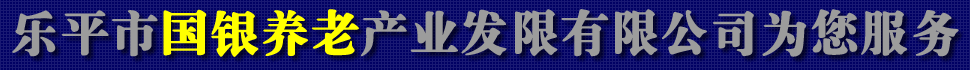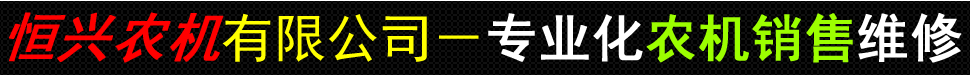新闻内容
沉溺范晓波
在邀省里的一位散文家为我写序无果后,神使鬼差,我冒然给范晓波打了手机。手机拨通了,一位南方男子的声音,音节短而柔和,我向他说明并表白之后,没想到,他竟同意了。合上手机,喜悦像一条心头的小溪。在我心里,他是经常翘首的才子。早在前几年,他在《散文》上发表的作品就准确清晰地击中了我的心房。他的文字像在河里淘洗过的沙子,洁净湿润,从不拖泥带水,而青春的记忆又带着别样的令人追怀、不忍弃之的伤情。
他的《悲伤的小号》,乡下的那个做教师的同学常常骑着一辆旧车,跑来和他讨论与生活无关,与精神有关的文学,这是印象中的一个细节。看似普通的述说却似针尖轻微地扎疼了我。因为忧伤因为无助,他的同学在文字中寻找慰藉,打捞支撑生命的那根稻草。还有一篇好像是他在广东一家企业时写的,文后的简介还有“经理”字样,写的好像是城乡结合处:垃圾,垃圾中的避孕套之类。我常常惊异他对生活的发现与界定,他对语言符号奇迹般的运用,就像把沙子淘洗成金子,令人眼前霍然明亮。
就这样慢慢记住了他。
他的文字如同琴弦在静夜微颤,看他弹吉它的照片,专注自恋,像一个男孩抱着自己喜爱的玩具。
他的眼睛与耳朵是忧郁的,他眼中含着水波浩淼的鄱阳湖,因风雨骤起而失去生命的麻雀。回忆中,故乡的树叶翻动出无限的美与感伤。而青春有时是狂放欢畅的,骑着山地车在乡下公路上奔跑时一边用美声唱着《我的太阳》。热爱歌唱热爱绘画热爱写作,对艺术的过分沉溺成就了范晓波。
2007年我请他给我写序时,他看我的简历,知道了我辞职的事情。他说他不赞成为了文学而放弃正当职业。我想,他以往的“漂流日记”中一定也充满了怀疑、茫然与黑夜里悄然发生的惊心动魄。
但我已控制不了这种惯性。2007年的10月,过了国庆节我便来到省城的一家报社报到。
范晓波在《南昌的孤独与爱》中写道:“不断的自我否定和勉励使每个夜晚变得动荡不安。——回到这个欠发达的中部城市,失去了高薪,却也没有职业上的安全感,全部的希望押在比天空还高远渺茫的写作上,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是在拿亲人的生存安全担保去猜一个也许没有谜底的谜。”类似的句子就是我现在病态中要寻找的良药,精神饥馑中要吃的食物和慰藉。为什么我们要离开原地,过上这种朝不保前夕动荡不安的生活。我呼吸到了那种此刻要呼吸的气息,也许是惺惺相惜。它离我的生活如此之近。某种程度上,它就是我的生活我心迹的翻版。我从他的句子中照出我慌乱的影子,闻到一股浪子飘浮的特殊的呛人的味道,它熏染了我的衣衫,脖子,衣下的皮肤,在我脆弱而坚韧的血管里游走。
一如我要依赖的精神鸦片,隔一段要读一读才解解瘾。然后长长地呼出一口郁积胸中的浊气。
远去的经典,女人书,都不能映照出我。而他出生、生长、生活的时代,所看的电影唱的歌曲则可共鸣共享。所以,我可以说,范晓波,你在酿自己文字的酒,却醉了那路上的客。
他笔下的文字是陷阱,大凡所有的好的文字都具有这样的特质吧。温柔的感伤,在水中浸过的文字,缭绕着他家乡鄱阳湖的水气,时时把心脏掏出来抚摸它的心跳。音乐不离他的生活。他的文字都带着节奏,带着吉它流浪的乐音。
范晓波亲手寄来的两本书放在枕边,一本《内地以地》,另一本《正版的春天》,他记录回忆了曾经的时代,时代里的温情蜜意,而里面始终有一条他行走的路线,隐隐的曲折的心脏奔波过的痛与诗意的行迹。躺下去,侧过身,习惯地伸到床头探摸到它——深绿色的书皮是《内地以内》,灰白封面的是《正版的春天》,仿佛插销插进了插座,我感受到一种震动的持续不断的沉醉的袭击。
尚新娇:《郑州日报》记者、70后作家。在《诗刊》、《散文》、《散文选刊》、《读者》等刊发表作品400多篇。着有散文集《空的那些》、《彼岸灯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