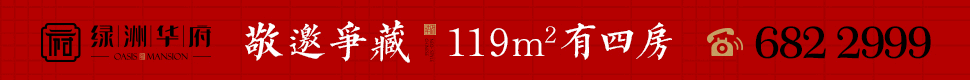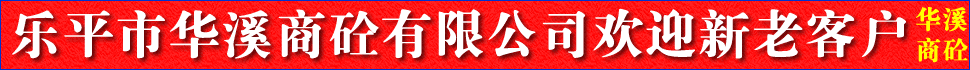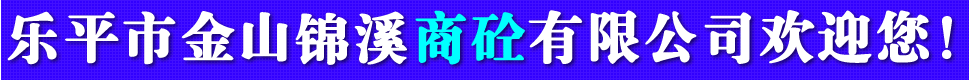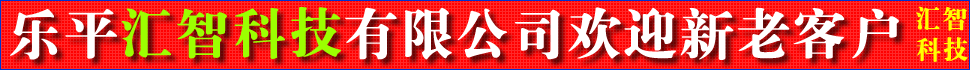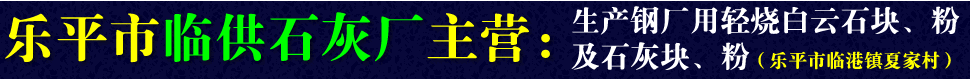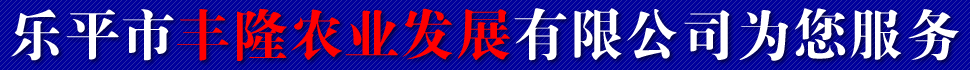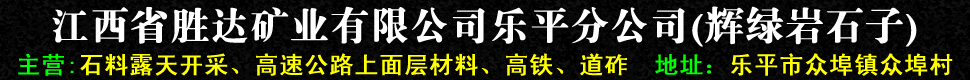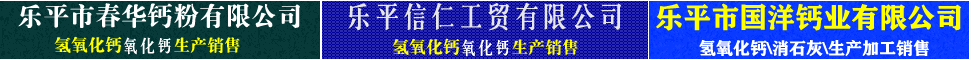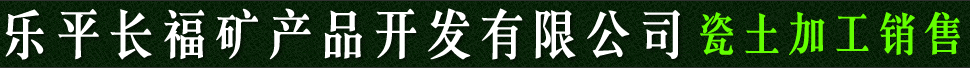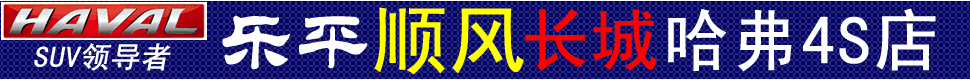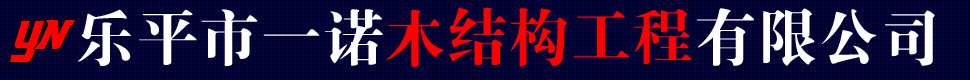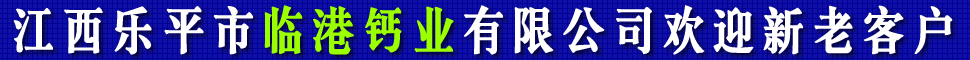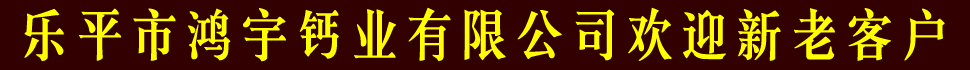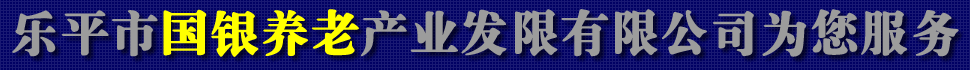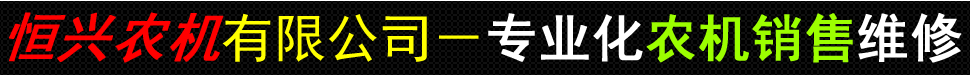新闻内容
范晓波的BLOG-悬空寺
上一次是在四年前,时间是四个半月,只是那时身份很单纯,只需对自己负责,不必对他人付出精力与感情。
如同读大学时,我甚至认不全班上的同学,更谈不上深交。
我要承认,对于群居生活,我一直是警惕和疏离的。其实和骄傲或孤僻都无关。我只是无法喜欢很多人,也无法让很多人喜欢自己。
20年前如此,20年后也无太大改观。
20年前的夏天,同学们喝着啤酒哇哇地哭,我在一旁漠然而怪异地看着,心里只有远走高飞的解脱感。
4年前的离别在风雪中,没有和任何人告别,路过走廊被两哥们瞧见,非要送我到街边打车。我们平常交流并不多,看见雪花堆积在他们的头顶,心里某个坚硬的东西被碰触了一下,但我不愿把这种情绪浅白地表达成感动,只是,伸手,帮他们掸了掸发梢的雪花。
然后,便彼此相忘于江湖。
这一次,虽然下水点和上次完全重合,但几千年前就有人说过,人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
我代表的不再只是自己个人。很直观的,我还要秉持委派我做管理的单位的立场。我必须做到来去都“一个也不能少”,还要把持住一个原则:“可以有故事,但不能有事故。”
我代表的并非个人,然而不可避免,个人的某些旨趣也会渗入工作角色。
在《进食的尊严》、《我喜欢写作,但不喜欢写作的人》、《一个没有情调的民族酷爱调情》等许多随笔中我都曾毫不隐晦地坦白过自己的洁癖。
骄傲、谦卑、深情、教养,我喜欢这些词各自携带的心灵信息,更喜欢能将这些品质并置一身的人。
我期待的集体生活并不以活跃为最高境界,我所乐见的是热烈而端庄。
这自然也不能说就是最好的境界。很抱歉,在某个特殊的时间段,我以自己的个人趣味影响了一群人的精神生活。也许只有我最清楚,这种影响在何时何地真实地发生过。
在有些人看来,我也许举轻若重了。
我默认了,只是,这样认为的人并不知道,我不仅要遵从工作角色,也要遵从内心的一些律例。
我并非只代表自己,同时,我也无法完全不代表自己。
这是此生第一次,对一群人产生关注并倾注爱憎。
我看见了这拨人的感动和理解,也明晰地感受到那几个人的不解和不满。
很抱歉,面对曲解和不满时我从来也不会选择主动解释和退缩,我的唯一反应只是,更加执着,更加强硬。
是的,从18岁开始,我就习惯了在孤独中强硬地推行理想。
不同的是,这一次,不需要像以往那样孤独。
我忽然也会担心离别了。
结业典礼上听学员发言,我发现自己居然落泪两次。
或许,我也习惯了这种像悬空寺一样远离鸡鸣犬吠并有终极信仰的生活。
6月12日在山西的悬空寺上,一面轻微地恐高,一面叹服于信仰的力量。
只送别了走得较早的仨人。
其中一位,隔着车窗目光仍像钉子一样钉在我脸上,然后,泪水滂沱。
我无法忍受这样的场景。
下午同宽厚的C院长、美好的Y老师等人交接完工作,在房间稍作调整,小心地躲过每一间开着门的房间,然后,提前2小时赶到机场。
办好登机手续后,短信和默契搭档了一个月的老师N辞行。
她说看见短信就想落泪了。她还一直在楼下等着我去告别,没想到人早已到机场。
我说我只喜欢重逢,不喜欢离别。
N同样是个美好且懂我的人,平常聊天并不多,见面基本只谈工作,最后一刻才说出,她能看出我这一个月的压抑与委屈。并表示,会尽快抽空到江西找我玩。
那一刻,我终于在离别的情节点上落入俗套:望着舱门洞开的飞机突然热泪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