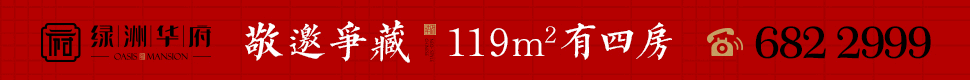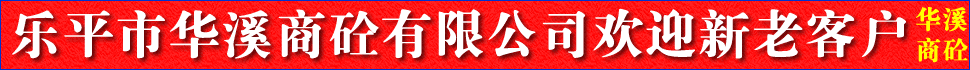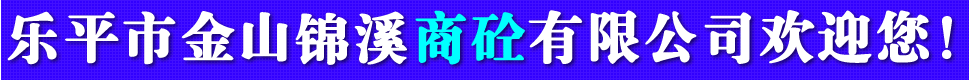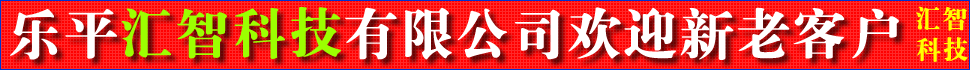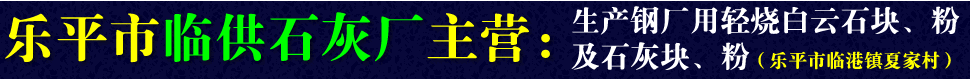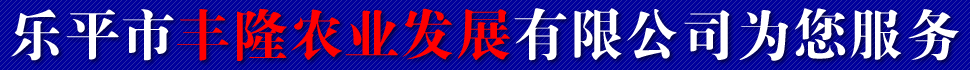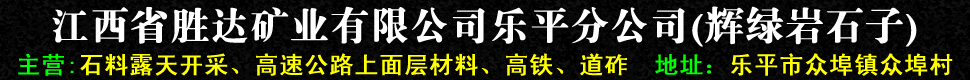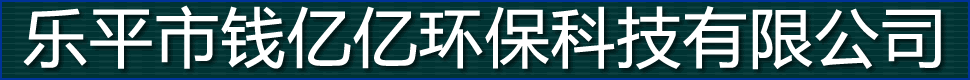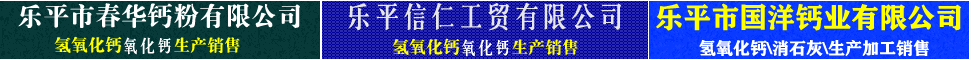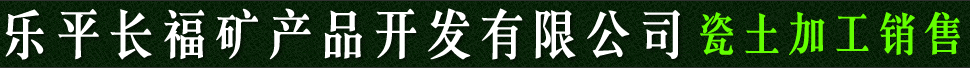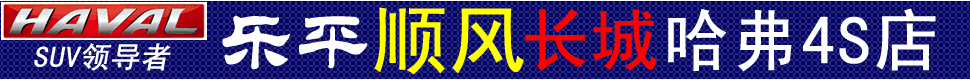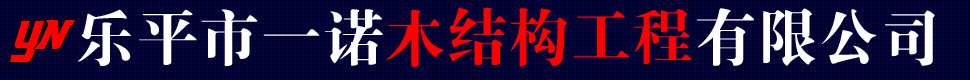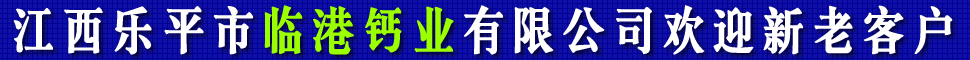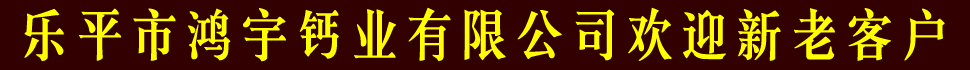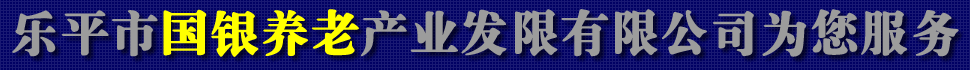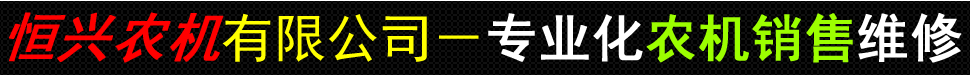新闻内容
范晓波的BLOG--民歌生长的地方
辽远、朴素、疼痛、隐忍、深情……
这是我对一些西北民歌的印象,这些词,后来准确地对应上了我在2000年3月中旬看见的陕北荒塬,以及西安以西的数千公里铁路沿线。
爱上那些歌曲十余年后,我来到它们的故乡。
那时江南已是桃花满天红,延安的早晨,气温却在零度以下,沟谷里到处是积雪和陈冰烙下的伤痕。我躲到火车站附近的旅馆里熬到太阳升起才敢出门。
在远郊的一座高塬上,我呆了差不多一个中午。那时太阳已经烤得毛衣里发躁发痒了,视界里仍是人迹罕至,只偶尔在黄土的皱褶里发现几只在坡上斜行的羊;或者,方圆数里内没有友邻的一孔独立窑洞。窑洞粗陋,却很感人地贴着红彤彤的对联,远远望去,像是深谷中一簇执着地开着的杜鹃。
这时,眼睛就忍不住激动起来,人也迎着响亮的阳光站起来作展望状。
一座座的塬不仅是黄土的集合,也像是由千万年的时光累积而成,它们在光雾中静默地此起彼伏,绵延不绝至天际。
不仅是眼睛,喉咙也跟着激动。明知性别和嗓音都不适合,还是忍不住叫了几句:“你若是(si)俄的哥哥哟, 招一招的那个手;哎呀,你不是(si)俄的哥哥来,走你走的那个路……”
那次行走历时半个月,回来后我告诉每个朋友:北方的山水确实比江南深沉质朴,北方姑娘确实比南方女孩更相信爱情。
时间过了9年。
这次也是近半个月,自北京往东,然后回身往北走,那些熟悉的定语,依旧在头脑里给我引路。
车过集宁后翻下卧铺,就着微微的天光打量窗外的原野。敛着呼吸,梗着脖子,从呼和浩特到包头,从包头到鄂尔多斯。
望不见毡房式的蒙古包。草原一铺开来,仍有种地老天荒的架势。几十里地才见一个低矮歪斜的土院落,院外站着几株沙柳,或者沙柳一样静立的驴马和人。已经是7月的最后一天了,早起的人身上还穿着薄毛衣或厚外套。铁路和高速路外的那些泥路,不知是哪个朝代留下的,真的就像鞭痕一样,歪歪扭扭抽打在原野宽广的脊背上。左一鞭,又一鞭,牧人的日子就在生存的驱赶下艰难地向前蠕行。
落住在鄂尔多斯一家四星酒店里。这个地级市因为盛产煤炭、天然气和羊绒,财政收入比中部许多省城都要高许多。本地一些钱多得没处使的人就长期包住在豪华宾馆里。这座草原上的城市离真正的草原有130公里远,换算成租车的人民币,草原离我还有600元距离。
有点点贵,但想都没多想就支付了它。民歌生长的土地一直是我急于朝圣的地方。我的青年、中年,我的思想、爱情,我在南方的许多次失意和得意,都曾得益于民歌的声援与扶持。
沿途停车加油时,就闻到了雨后弥漫在空气里的花草的甜香,真正到达鄂尔多斯草原时,却惊讶于它的贫瘠和干旱。草只比脚踝高一点,遥看成片近却疏。沙蒿和骆驼刺丛间,到处是蜥蜴状的小动物,似乎草原原本就是在沙漠上长出来的,或者,草原在沙漠的追赶下渴得不行,正匍匐着苟延残喘。骑着马往生态保护区的深处走,地表的绿色才稍稍茂密些。
草原毕竟还是草原,天,比想象的更蔚蓝,云,比期待的更白更低,不时在地面掠过一大片阴凉。牧民的笑脸,明显比南方小贩宽厚慈爱得多,你把玩了半天也不买他的弓箭和酒囊,他仍憨厚热情地望着你,请你坐下来喝免费的奶茶。
以骑马的借口到的草原,到达之后,才觉得骑马并非最紧要的事。马队每停歇一次,我都要跑到无人处,眯着眼使劲往四野张望,倾听。
除了裂帛似的风,除了绵羊啃啮草茎的脆响,除了云影下一只鹞的羽翅的震动,除了皮肤在正午的烈日下嗞嗞地冒着油,草原上什么声音也没有。
蒙古长调,要等晚上开篝火晚会时才能听到。我并未预订水泥建的蒙古包,也不打算参加这种旅行社组织的狂欢。
据说,最丰饶的草原和草原文化在数千里之外的呼伦贝尔,同时也听说,在七八两个月,呼伦贝尔的游客可能比羊群还多,周末一张铺可以卖到一千五百元人民币。
不过,鄂尔多斯已经让我这个江南人震动了,我不时在心里拿它同刚刚离开的北戴河海滨比较。
海边越是喧嚣
人心就越是安宁
草原越是安宁
人心就越是喧嚣
同样没有边际
草原的辽阔并不是床
草原从我的视线里拧出水来
浇灌它的干旱和孤独
在心里筹划着下次去呼伦贝尔的行程。不过并不奢望去那里听民歌,在陕北、内蒙、青海、新疆这样的地方,我只需看见质朴和苍凉,以及一种欲歌欲舞欲醉欲哭的冲动。那里生态保护得再好,也留不住比这种生态更易逝的行吟般的生活方式。说到底,民歌是乡土对农耕社会的馈赠。
这个时代,民歌更多存活于怀念和少数天籁般的嗓音中。
对当今这个排行榜比股市还虚火的乐坛我实在没有太多好感,在沙尘暴般阵性发作的流行音乐和各种商演的围剿中,民歌的生态困境,比草原还要严重。
对于未来的漫长时光,传统民歌生存的最大危险不是被遗忘,而是动机各异水准各异的种种翻唱。那些形形色色的伪民歌手和时尚组合,唱完了自己的原创歌曲又不甘心匿迹时,就搜出我们记忆里最完美的那些旋律来肆意挥霍。
这样的翻唱,看上去是继承,本质无异于绑架和谋杀。那些水泥地上生,水泥地上长的人,心肠也和水泥一样干硬,放歌的热情主要源自虚荣和实利。这样的歌者,怎么可能体察并唱出荒塬和草地深处的疼痛、隐忍和爱恋?
在我刚开始接触流行音乐的那些年,每当父母偏激地把一些劲歌辣舞斥作佯癫和抽风时,我也会偏激地认为,不能接受流行音乐就是衰老的标志。
其实我们都忽略了一个事实,无论艺术是多么主观的东西,它的审美也都存在一个相对客观的度,流行音乐和民歌也是如此。
我在歌厅里热烈追随着1980年之后的流行经典,同时,也在MP3和家庭音响里珍藏着陈酿般的民歌经典。不过我对经典的定义,远比媒体和音像公司要苛刻。
这些歌每首都听过至少10个版本:
《在那遥远的地方》我只认吴雁泽,其他的,要么太华丽,要么太轻佻。《赶生灵》的最高值应当是冯雪健,普通话和方言糅合得恰到好处,换人唱立马走味。《半个月亮爬上来》这支歌,以前总找不到标杆,大约是去年吧,忽然在网上搜到彭丽媛的版本,音色柔媚深挚,仿佛镶着月光毛绒绒的银边,每听一次,心脏都有被惊艳洗掠的幸福感,从此只听这一版。《可爱的一朵玫瑰花》无数歌唱家唱过,最打动我的却是一位姓氏不详的大学音乐教师,在人声嘈杂的相亲大会上,他站在边缘阖着眼自语般地清唱,听得我皮肤发凉,内脏发热。
许多年了,总想再邂逅这位歌者的声音而始终未果,这样的惊鸿一瞥似乎在暗示:民歌尚在民间。
荒塬、戈壁和草原是北方民歌的发源地,它的不衰,还要靠这些贴着地面呼吸的嗓音。民歌在时间深处孕育,成熟,然后,顺着这些卓越的嗓音,向远处流传。
关注范晓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