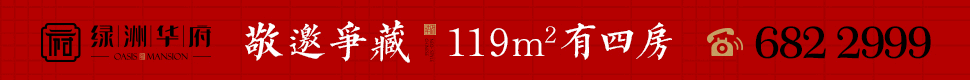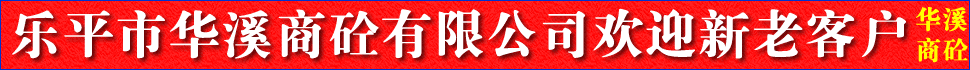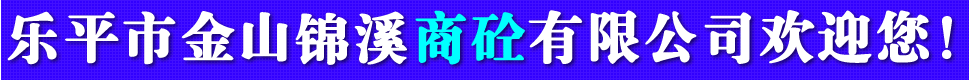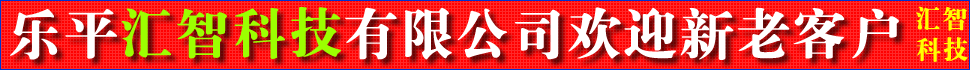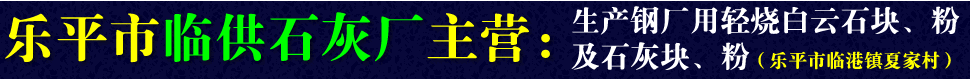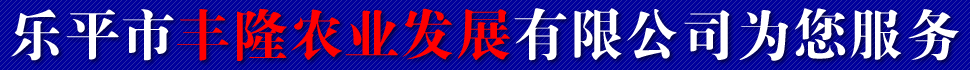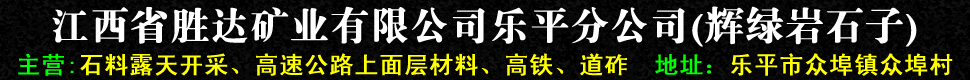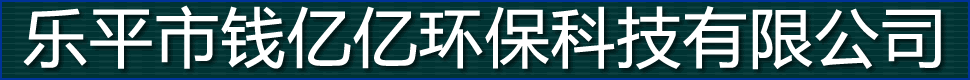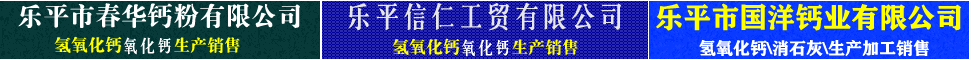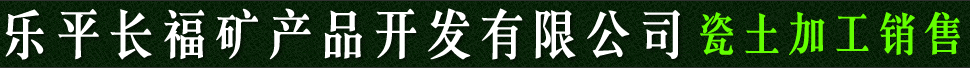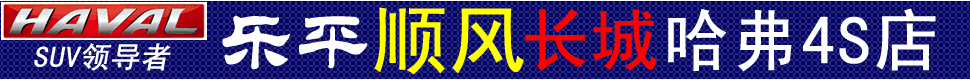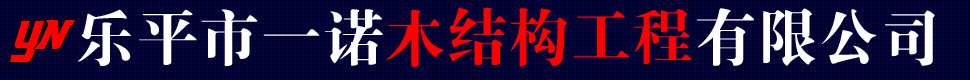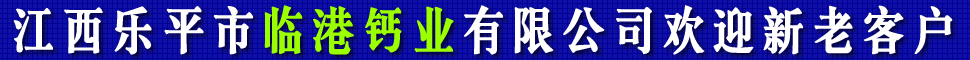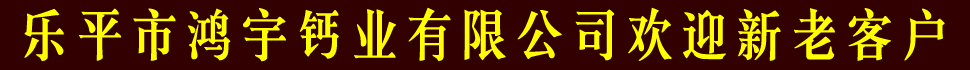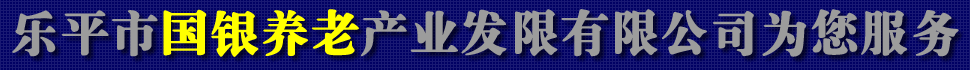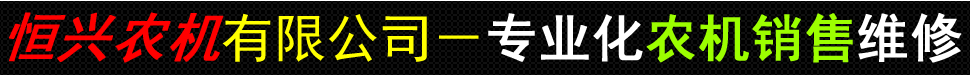新闻内容
范晓波的BLOG--客自中原来
十多年前我初到南昌工作时,认识了一些赣南人,从他们那里接触到客家人这个概念。当时的感觉是诧异而懵懂的,明明也是汉族人,却非要单列出来说,给人少数民族的错觉。那些人自称客家时的神情也是有些微妙的,说自豪或许有点夸张,某种与众不同的自得感还是有一点的。
他们平时也说普通话,彼此一见面时立马切换语音频道,像要用方言竖起一道篱笆,把我们这些讲普通话的普通汉人排斥在外。后来回忆起来,这些人真有不少交集:老家都在深山里,物质上能吃苦,精神上很敏感。像沙漠上的狐獴,不时立起身子警觉地探头打望远处,有时甚至有点草木皆兵。一旦确认你是有善意的,他便会刀锋入鞘,赤诚相待。
交际圈里的客家人一点点多起来,特别是当一些我们原本很熟悉的军政名人也被指认为客家人后,就有种恍然大悟的感觉,其实客家人一直就在我们身边,只是缺少特殊的标志,过去没有意识到这一重身份而已。
学者们比较一致的看法,客家人是自西晋末年(公元四世纪)开始,从以河南、山西为中心的黄河流域分五到六次迁徙到赣、闽、粤以及湖南、四川、台湾、海南等地的,原因主要和战乱与饥馑有关,比如黄巾起义、五胡乱华、黄巢起义、蒙古南侵、明朝灭亡等,每一次大的动荡都会催生一次大规模迁移。
目前,全国有16个省共228个县有客家人居住。在江西,纯客住县、市有宁都、兴国、赣县等18个,非纯客住县、市有赣州、万载等20个,客家人口总计1000多万;福建客家人口近400万,纯客住县有长汀、连城等8个,非纯客住县市有建宁、沙县等21个;广东客家人最多,共有2000多万,纯客住县、区、市有梅江区、梅县等18个,非纯客住县、市更是多达66个。海外的客家人也多达五六百万,约占华侨和海外华人总数的三分之一。
客家人的来源和迁徙线路也许是比较清晰的,不过我心里始终想不清楚的是,长江流域.的汉人,不少也是从别处迁来的,为什么他们没有成为某个民系,独独客家人自成体系,以至于在时过境迁的千百年之后,仍自称客家人呢?是由于他们慎终追远,敬重祖先,还是因为他们始终保持着居安思危的危机意识?毕竟,千年之后,这些客家人在客居地早已反客为主,成为当地的主人或主人之一。
2008年岁末,出于对客家围屋的好奇,专程去了趟赣州市的龙南县。龙南是全国现存围屋最多的县,保存完好的有500多座,最出名的是县城以东15公里外的关西新围,建于清代嘉庆至道光年间,是关西名绅徐名钧兴建的,前后费时29年。围屋占地面积7700平方米,配套的附属设施有10000平方米。整个围屋呈长方形,四角立有4个高耸的炮楼。围屋外墙高10多米,壁厚1米。整体建筑五组排列,前后三进,共14个天井,正中为祠堂,对称分置18个厅,围内通道贯穿各列建筑,百余间房屋有序分布。
围外的朴拙坚实和围内的画彩镏金的精致风格相映成趣,就像一个甲壳虫的坚硬外壳和它柔软的内脏那样反差分明。
另一处的客家酒堡规模较小些,整个围屋南北长 55米,东西宽45米,占地2475平方米,距今也有200多年历史,围内建有许多三层结构的民房,共有住房126间,另建有炮楼4座,炮楼四周布满枪眼。围内曾常年储藏可供全体居民食用3个月的粮食和米酒。
据考证,围屋的母本系东汉中后期中原大庄园主居住的坞堡,中原士民南迁时,把这种建筑形式和技术传到了赣南以及福建和广东,又因地制宜做了一些发挥。在赣南多为四方的围屋,在闽西则化身圆形的土楼,主要强化了建筑的防御功能。有的围屋内墙还涂刷了一层粘性极强的糯米,一为加固墙体,二为应对不时之需,如果被困太久围内断粮,就用刀把糯米刮下来水煮充饥。
看得出来,即便在南方繁衍了数百年,客家人对于身处的环境仍是心怀戒备的,他们既要融入当地的山川,又不敢彻底敞开襟怀,总担心有不测之风云起自山林之内或青萍之末。围屋外紧内松的建筑学特点正是这一复杂心理的外化。
到了广东,客家人算是站稳了脚跟,不需要把日常空间局限在完全闭合的土墙内,便将围屋的一边敞开,建成中原府第殿堂的模样,并在门前设置一处晒物的禾坪及一口半圆形池塘。池塘汇聚围内各个天井的排水,既可以养鱼浇园,又可以充当消防水源。所以,在梅州一带,我们看到的多是这种殿堂式围龙屋,实用性和美观度都比赣南围屋和福建土楼有所提高。
我到达那些围屋时,它们的主人早已搬离,融入城市或乡间洋楼。围屋内的生活形态、伦理关系和烟火气也一并灰飞烟灭,我必须借助资料、道听途说的故事,加上强劲的想象,才能还原空寂的围城中曾有的拥挤与热闹。
从内宽外窄的射击空望出去,田野是一片虚虚的绿,亮得晃眼。酒堡的黄昏,光线晦暗,站在哪里照相都会曝光不足。只是,书着繁体酒字的大红灯笼呈弧形排列成一圈,多少稀释了一点堡内的暗淡与沉闷。
南迁之初,客家人常与土着和盗匪发生冲突,这强化了他们的身份意识和宗族观念。
客家人的族长并非世袭,由族人依据辈分、威望、能力、品行等要素公开推举。围屋内的小社会便是以族长为龙头,以族规为准绳有序地运行,这样有利于发挥合力,一致对外。
这个小社会的财富有着族产和私产之分,二者并存不悖,在族规的框架内各自发展,有种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兼容的意味。不过说到底,围屋本身还是封建割据意识的建筑象形。
一位客家朋友说,围屋里虽然住着许多小家庭,但因建筑格局和管理模式的影响,并无多少私人空间,居民之间很难有隐私,一家吵架全围人都听得清清楚楚。在这样的环境中,那些特立独行的思想和观念,常会受到孤立和排挤,这种生活形态对人的创造力还是有些钳制的。
的确也是,客家历代名人中,像陈寅恪这种才学与人格均孤绝于世的名士似乎并不多。自然,藉此就把责任归咎于围屋的生存方式或许有点直线思维,要说一点关系都没有也难免牵强。
看过一位客家籍作家写的客家人性格分析,谈到客家人的优点不外乎勤勉、自立、自强等,毛病则包括:过度自尊,太看重面子,容易得红眼病,陷入内耗,作者还沿引日本学者打的一个比方——三个日本人斗不过一个客家人,但是一个日本人可以斗过三个客家人。
同我个人对客家人的切身感受有不少暗合之处,不过内耗的性格弱点,放到其他汉人身上也基本适用,所以究竟具有多少族群的共性,还真的不好考量。
在我看来,客家人坚韧的开拓精神和柔韧的适应能力倒是有据可考的。
“逢山必住客,无客不住山。”作为后来者,在生存空间的选择上没有话语权,只好在土着的领地边缘伺机置喙。在南方,这种边缘就是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从那些纯客县的地理位置可以看出,基本在赣南、闽西、粤东交界的山区。
梅县雁洋镇的桥溪村位于阴那山五指峰的西麓,海拔近千米,在明朝之前是纯粹的荒山野岭,大约在明万历年间,客家人在此建村,香火延续至今。
现今这里正打造休闲度假村,铺了水泥盘山公路,上一趟山仍然不易。从山脚到村前这段路我差点晕车呕吐了。村子就像悬挂在山壁上,找不到一块稍大点的平地。就算到了村前,每走一步都要弯腰埋头努力向上攀登,状若叩头,所以这个村子还有个别名叫叩头溪。当然,村里人对于叩头溪的来历还有一种说法:明亡后,朱三太子一路南逃,曾躲到此处隐居,本地官民前来朝拜时,均要一步一叩头,故得名。事实似乎也在佐证这点,本村人大多数都是朱姓。
不管哪种说法接近真相,都从侧面印证了这一带的偏避和艰险。在公路开通之前的年代,进一次村和出一次村都像是一场远征。
在一马平川的黄河流域住惯的人,要搬迁到陡峭的山坡上居住,还要克服气候、外敌骚扰等种种干扰,需要多大的毅力和适应力呢?这甚至都不是几年几十年的坚持,许多习性和基因,要花费几百上千年的时间去改造吧。
那些为捍卫生存权而爆发的大大小小的战役和械斗,地方志和族谱上多有记载,征战的难度尚在明处,成功了就地落户,失败了另辟蹊径,虽则凶险,倒也干脆。在我看来,最难的还不是社会关系的楔入与重构,而是对于全新地理环境、气候环境的征服与适应。这种适应貌似仅仅关乎生理,其实有着太多文化和人类学的内涵。
十年前,我也曾有长居珠三角的尝试。我故乡鄱阳和那一带的纬度相差不算太大,但不大的纬度差造成的气候差异、植被差异已让我浑身不适。首先不适应那里四季不分明,一年似乎只有夏秋两季,生理机能和心理机制都被打乱。那些躯干低矮、叶片肥厚、花瓣鲜艳的热带植物明明也很有风韵,可我再怎么跟自己做思想工作,就是喜欢不起来,觉得远不如江西的樟树、桃树来得亲切。这些最终成为我选择还乡的重要原因之一。
2012年12月初,在梅州逗留四日。和我预想的不同,梅州的生态环境好得接近江西,同我去过的广州、顺德、阳江等地完全不在同一层面。城市也干净且安静,鲜有工厂,也极少外来人口。上下班高峰期也不会堵车。穿城而过的梅江迂缓宁静,弧度肥美,像梅州人那样,心有静气,步履从容。
有天夜晚我沿江慢跑,十多分钟都遇不上一个肩膀擦身而过,只有温湿的江风软软地舔舐着面颊的皮肤,间或还能闻到桂花的浓香。
才晚上十点多,梅州的街面便人影寥落了。同喜好夜生活的潮汕地区及珠三角的人不同,梅州人大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方式相对科学和健康些。
已作为景点开放的梅县南口镇桥乡村,因旅居海外的华侨众多,建筑可见客家和西洋两种风格的合璧。周边的田园基本保存完好,山是绿的,水是清的,一些番鸭畅游浅塘。农田有些布满浅黄的稻茬,另一些被种上进口草皮。我在“南华又庐”前闲逛时,几个农民正戴着遮阳帽搬运草皮,说是准备卖给楼盘和公园,收益自然比种粮食高不少,因为价格高成本低,一年可以种很多批次。
下榻的宾馆是本地一家有名的庭院式五星级酒店,院子里密集栽种了各种好看的热带和亚热带植物:大王椰子树、高山榕树、木棉、秋枫、晃伞松、芋荷、凤凰树、黄槐、爆仗花。基本是岭南才有的品种。
宾馆外有一处村落叫东升村,隶属于梅江区三角镇,离开梅州的前一天下午我去那里走了走。东升村的房子已无多少客家老屋的特点,稍老点的房子都是民国时的南洋式楼房。房前屋后疯长着高大的芭蕉和累叠着青色果子的蜜蕉。
一个老人在村口用网兜打捞鱼塘里的枯叶和杂物,问他这个村子是否都是客家人,他点点头,又问他们祖上是哪里迁来的,便没了耐性,让我到前面的宗祠里去打问,不知是我的问话方式太鲁莽,还是他确实不关心祖先的来历。
客观地说,作为世界客都,梅州的城市和乡间都堪称漂亮,但置身其间,当年前那种客居珠三角的茫然和不适感再次卷土重来。尤其在宾馆的庭院散步时,那些热带植物的浓重的身影与气息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提示我的外来者身份,一个在樟树、枫杨下长大的江南人,只有在香樟的清香和油菜花的粉香中才能安恬陶醉地呼吸。
这也让我推想到客家人初到梅州时的困窘。他们的籍贯和性情离这片土地比我还要远很多,那些在大槐树、榆树和白杨树下长大的人,是怎么接纳并习惯这些外星景观般的热带植物的呢?黄河流域的四季温差可是比长江流域还要大很多,他们怎么适应得了一个个无雪的冬天和岭南的闷热与瘴气呢?除了改变自己的心态、肤色、劳作方式,还要完成哪些我们无法洞察和归类的基因改进呢?在我看来,这个工程远比和土着及土匪打十场战争还要辛酸漫长。
中国人写的历史书,每谈到战乱导致的流民迁徙时,总喜欢加上一句:客观上加强了东西或南北地区经济与文化的交流。每每看到这样的结论我就会觉得,那个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历史学家真是可恶,这种貌似客观的历史观其实是建立在漠视具体生命的精神苦难基础上的。
在梅州,我总是有意无意地和当地人扯到乡愁这个词,可是对方大多比较淡然,和我交谈的客家年轻人说,他们世代居住此地,并不存在什么乡愁,现在再回到中原去反倒更不习惯。
他们的说法应该是诚实的,一般说来,有乡愁也是第一第二代或顶多第三代移民的事,不会此愁绵绵无绝期。总的说来,中国人算世界上最务实的人种之一,生存需求永远大于情感需求。
不过有意思的是,一个不谈乡愁的族群,定居异乡千百年后,却一直乡音不改,以至于时代更迭了无数回,与当地语言杂交了无数回,他们的口音仍旧和古时中原的祖先相差不多。他们迄今仍称绳子为索,脸为面;称吃为食,走为行;称脖子为颈,柴为樵……他们迄今最流行的一句话仍是:ai(发第三声)是客家人,那个ai所对应的指称“我”的汉字,古旧生僻到现代汉语词典里都没有收录。
基于这种对于方言的和客家身份的看重,我又一厢情愿地认定,客家人心理其实是有乡愁的,只是这个乡太远,愁太深,消溶进血脉,自己都意识不到了。或者说,深到了无的程度。
实事求是地说,宾馆里提供的客家菜并不好吃,既无粤菜的清淡,也无中原菜的厚重口味,多是杂烩和折中的产物,比如盐焗鸡、枣姜羊肉、米粄等等。
在梅州的四天,每顿都会吃到的一道菜是酿豆腐,在豆腐里放点肉馅烹煮而成。我的第一感觉是,这种怪诞的搭配绝对不是从口味出发的。一打听果然不假,客家人初到岭南时,很怀念中原的饺子,但岭南不产麦子,没有米粉,他们就把颜色和米粉相似的豆腐当成米粉做成酿豆腐。
酿豆腐的味道和饺子毫不相干,不过每次吃饭时我都会品尝一块,因为每次夹起这只义饺时,眼前就会浮现一片北方的麦田,那麦田地势平坦,无边无际,六月的熏风追逐着金黄的麦浪,一波一波地涌向古铜色的天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