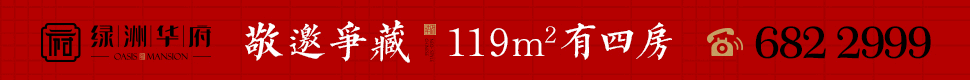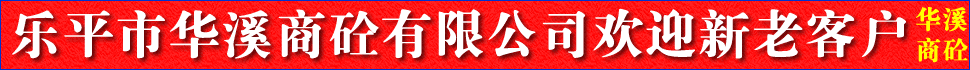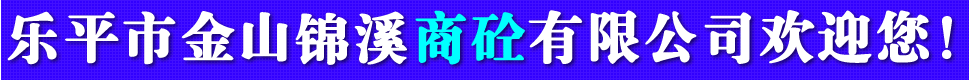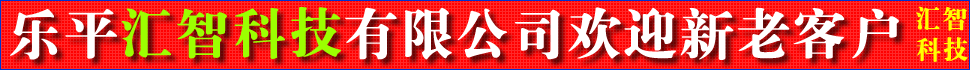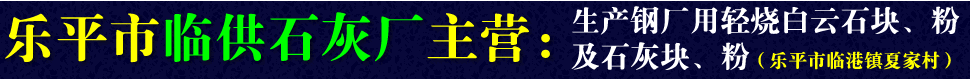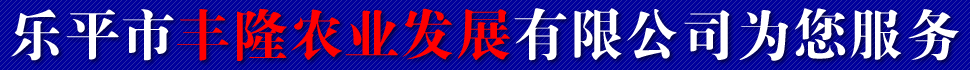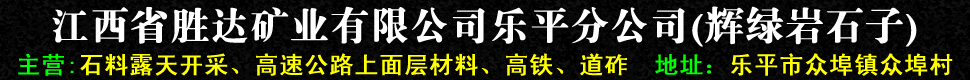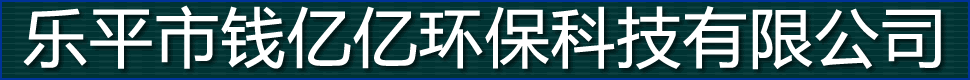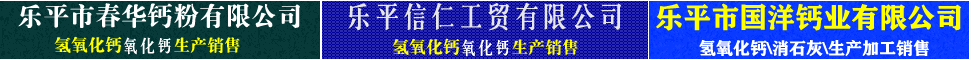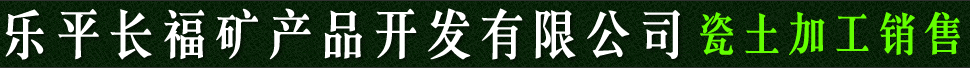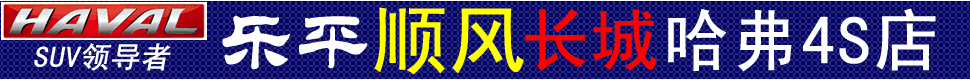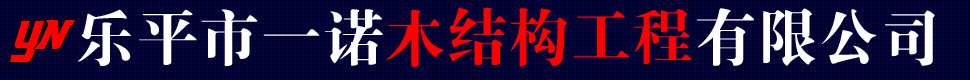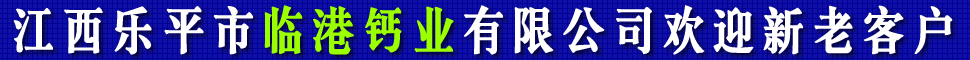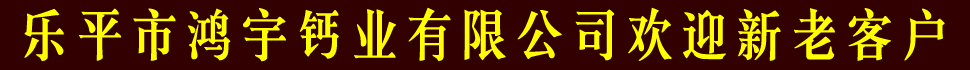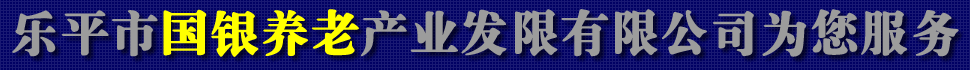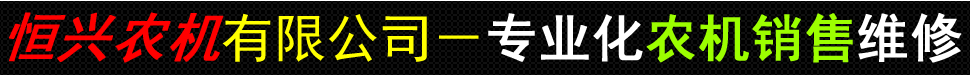新闻内容
范晓波的BLOG:开门见樟
如果适当夸张一点,再稍稍矫情一点,我似乎可以这样说,春天的清晨,我是被樟树的甜香熏醒的。
在我醒来前的一两个小时,樟的呼吸从阳台外的树梢蒸腾起来,一波波地汇聚拥挤在阳台上,被一面巨大的咖啡色帐幔阻隔着,像水库内的水位越涨越高,随时要冲开帐幔一样。
香情如此紧迫,我醒来的第一个动作不是去卫生间,眼睛还未完全睁开就赤着脚去扯隔开卧室和阳台的的帐幔。哗的一声,樟花亮灿灿的浓香就和晨光一起破空而入,像绝堤后的水瀑,瞬间将人淹没,不用吸气都会呛入口鼻,浸透肺腑后,在体内久久萦回不散。
这是我在这个没物管的小区坚守十年获得的唯一回报,楼前的小樟一年年地长高,从一楼到二楼三楼四楼,头顶快齐平我家阳台。
樟一直生活在周边,我对樟的倚重,却远迟于桃树和李树。我前些年才注意到樟树也会开米黄色的花,近几年才迷上樟的气味和隐秘身世。
外公的老家祥环,村东的路口有三株大樟树,村西的路口也有一株,腰围须三四个成人合抱,没人说得清树龄,至少在百岁之上,可能是建村伊始栽下的。
我对它们印象深刻原因有三:一是作为路标。幼时总以跟着大人走路为苦,枯燥没自由。去祥环的路上,每上一道坡就要抻脖子瞭望,等望见绿油油的色块里蘑菇云般高出的那一簇,就松了口气,接下来的路途有如雀跃。
二是作为休闲地。村中少年,热天可以群聚的地方除了水塘,就是老樟的浓密树影。正午大人都在屋内的竹床上打鼾,少年东倒西歪在老樟下的草地上,咔哧啃着刚从菜园里摘来的黄瓜,用狗尾巴草掏耳朵,议论村中美少妇和远山洞穴里的老蛇精。一条水牛被拴在树根上歇昼。樟的根大部分埋在土中,也有老根虬曲着身子挣出泥土,在地面弓成小独木桥,又从另一头扎入土中。中空的部分,正好系棕绳,打的却是活结。牛贪凉,或站或卧,压根没有逃的意愿。牛半阖着眼,刷牙般流着浓稠的白沫反刍早晨在田埂上吃进胃里的草根,身子被牛虻的吸管叮破时,才会睁眼神经质般闪动一下黑亮的牛皮,把蚊蝇从身子上甩开。
三是因为神秘。面对水塘背向菜园的那株,根部有座石神龛,一年四季,龛里的黄土都插着些残香,不知祭拜的是土地公公还是樟树,反正我们从不去那里打闹。立于土崖背靠山林的那株,被各种藤本植物纠缠拖累得身躯佝偻,极像面容阴沉的老婆婆,根部的泥壁被水牛蹭痒磨出一人高的泥洞,白天长期被水牛占着,晚上黑洞洞的挺吓人。从军多年的外公说,那里面藏着个国民党空降来的特务。特务天天躲在里面,那他吃什么呢?我问。吃泥巴。外公做出伸手抓大把泥巴入口的动作。我居然深信不疑,从没敢靠近那株老樟。
祥环附近的村落,村口大多也有老樟,起初我以为是巧合。成年后在南方乡间漫游,发现但凡有些资历的老村,村口基本都有古树,非樟即枫,以江西为例,多数为樟。然后知道一个说法——水口,这是风水学的概念,实指村头水流进出的地方,暗喻财运和村运。古樟一般伫立水口,是守护村庄的风水树。正因为如此,它们能躲过刀砍斧劈,得到世代的保护和敬重,最终与村庄同寿。
有段时间,常陪民俗专家去一些着名的古村看老建筑,研究古戏台、古祠堂和深宅大院。那些建筑雕梁画栋,多是几代人接力完成的,镂花的门楣与窗棂刻录着手工艺术的辉煌和十年磨一剑的匠心。我留恋老宅内时光的慢,却不太爱那些老房子。起初是因为阴气重。不管徽派瓦房还是客家围屋,结构上均不以采光为优先考虑的因素,思谋的重点是风水和防盗,空间昏晦低迷,抑制人的激情。加上久不使用,少了人气和烟火气的浸润,阴沉得像一座座废弃不用的电影布景。后来的不亲切,是发现那些能保留至今的老宅院,基本是官宦富贾的家产,作为文物,他们纪念的是豪门望族的生活情趣,并不能代表广大的平民。
平民家的土墙和茅舍无力穿越两三百年的风霜雨雪走到今天。专家在板壁上寻找刻法不一的九十九个寿字,或者查阅黄得发霉的族谱时,我就去村口的大樟树下等待。在樟树婆娑的绿影下眺望白亮的水田和冒烟的土路。或者,蹲下身跟一只躺在树荫里乘凉的土狗交换眼神。在我看来,古樟树比老房子更能代表村庄的精气神。老宅里的木头全是死的,樟树仍然活着。老房子讲述的是村中富人的发家史,老樟则记得每个生于斯,死于斯的村民。如果记性再好点,它应该还想得起每个从身下走过的客商、小货郎、乞丐,当然也记得星夜潜入村落的土匪和小偷。
有次去龙虎山一个号称无蚊的村落,考察了很久,果然没一只蚊子。究其缘由,说法各一,后来在村后发现许多樟树和桉树。有人就说,和桉树一样,樟树的香气可以驱蚊驱虫,樟脑丸的主要成分就是从樟树的枝叶中萃取的。大家还想起一桩旧事,当年在江西下放的上海知青,返城时带的最受欢迎的礼物就是樟木箱,不仅防蛀,驱霉隔潮,所放衣物还会散发出好闻的植物香。有的地方还有相关风俗,女孩出生时种下一株樟树,等她出嫁,就把樟树伐倒制成樟木箱子做陪嫁。
大约从九零年代开始,南昌的绿化树从法桐变成香樟,二十年过去,许多街道都撑起了绿色穹顶,四季不褪色也不凋败。这就是樟树的优越之处,到了冬天也不脱叶,对灰尘和空气中有害物质的吸附能力也强于法桐。因自身有异香,不易生虫,还省去了喷药养护的工序。唯一烦人的是冬天会落籽,那种乌黑浑圆的樟树籽,汁液饱满,砸在车顶,宛如一颗颗微型水弹,嘭的一声,黑汁四溅,涂在车顶和挡风玻璃上,干结后清洗颇为费劲。落在地上的,貌似打翻了几箩筐的黑豆,一眼望不到边,脚踏上去,噗嗤噗嗤地响,浓香就喷散出来,比樟叶、樟花香十倍,味道潮潮的沙沙的,浓烈程度快赶上刚锯开的樟木的横断面,隔着几米远就能看见香味在空气中散逸的弧线。刚学会走路的孩童把它们当气球踩,哪里樟树籽多往哪里走,用此起彼伏的爆裂声宣示着脚力和成长。乌鸫和斑鸠也特别爱吃樟树籽,在树影中低低地掠来掠去,三个一群两个一伙地抢食,人走到面前,歪头翻眼,瞥见你手里没带气枪就浑然不顾,真有种鸟为食亡的忘我。
城里的樟树大多是半路出家的,加上种植密度大,很难形成如伞如盖的气度。我只在省政府大院和郊外的农大及核研究所见过成片的樟树,几十株整齐地排列,遮天蔽日,雨不太大时穿行其下,都不怎么会湿身。阵容过于庞大和整齐,造成了营养上的互相掣肘,谁也很难高出一头,最大的胸径也不足一米。为了争抢阳光,一个个踮着脚尖往天空奔蹿,发育得瘦长笔直,无姿色也无风度。这让我时常想起乡间的野生老樟。每次在户外周游,都特别留意它们的身影。
这些年顺道或专程拜会过许多老樟,少则数百岁,多则千多岁。印象深的有几处。
离南昌最近的一株是安义罗田古樟,直径三米多,树龄有一千二百年,相传是罗田村始祖黄克昌所栽。位置在古时安义到南昌必经的驿道旁。黄始祖逃难至此,在山坡上搭棚暂住,夜间梦见金狮入土,天亮后受梦的启示,从金狮入土处挖出宝贝三百斤,便栽下此树做纪念。村落里没有可信的编年史,宗谱连女系都可忽略,更不会为一棵树写传。这种传说,不知是哪一代人的附会。反正没人活得过那棵树,也就没人说得清它的身世。
人逾百岁成仙,树活千岁成神。古樟的枝桠上挂满了写着各种心愿的红绸带,低处用手系,高处的,是绑了石子甩上去的。微风拂来,庞大的树冠便发出沙沙的下雨般的声响,树叶通了电般飞快地抖动,红绸带也吉祥地飘展开来。有的游客双手合十,闭目绕树走三圈,口中念念有词,像草原上的人祭拜敖包。
最老的一株是婺源甲路乡的古樟,地处严田村,树龄一千五百年,腰围需十多人合抱,树冠冠幅达3亩,旁有溪涧古桥,是展现江南古村落水口文化的着名景点,也是最适合摄影构图的一处古樟树。树下有可供食宿的仿古庭院。远望无人干涉,走近须买门票。古樟的身份牌上写着:宋高宗赵构被金兵追杀时曾匿于树冠逃过一劫,后下旨封之为神树。当然,类似的情节在别处的名树履历里也时常看见,故事的主角要么是倒霉的朱元璋,要么是更倒霉的宋高宗。
面积最大的一片野生古樟林在泰和县的麻州,麻州位于泰和县城南面的塘洲镇朱家村赣江边,又称金滩古林,占地一百多亩,约有古樟五百余株,树龄大多在四五百年以上。此处我先后去过多次,它的特异处不仅在于规模大,绿境幽深,更妙的是,随处可见巨树倒伏在林间小路上,被雷劈倒,或者寿限已到自然死亡,有着别处樟林罕有的原始性状和蛮荒感。可惜被开发商盯上后,最终也沦落为喧闹的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