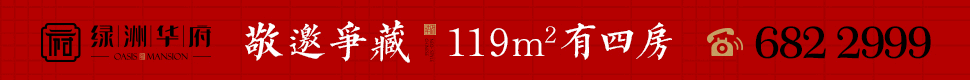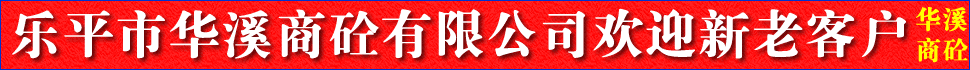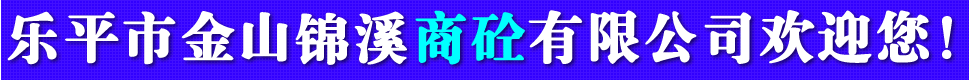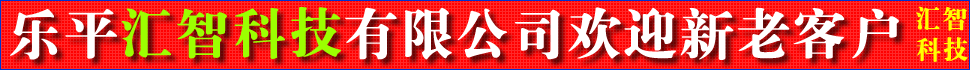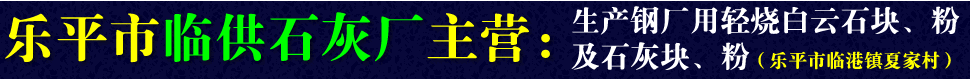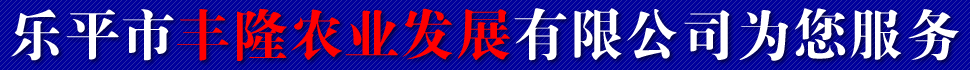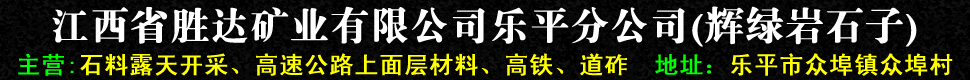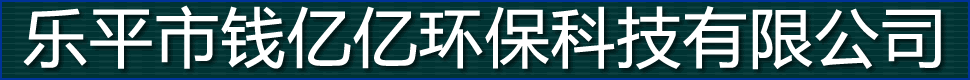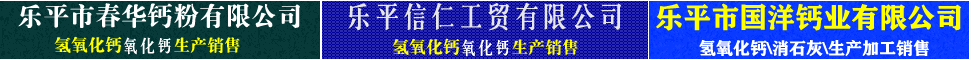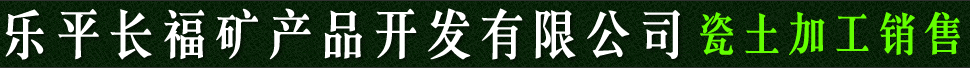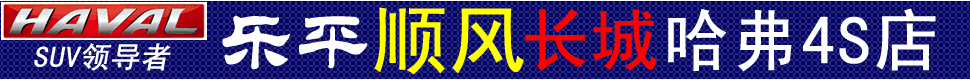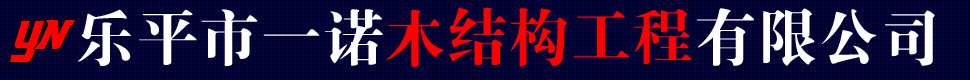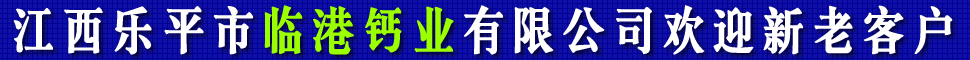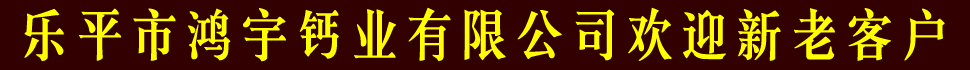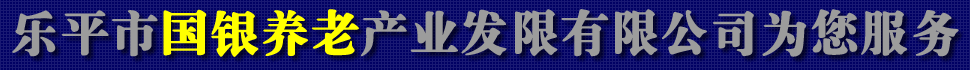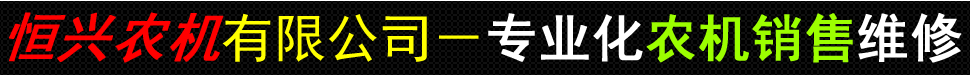新闻内容
县官文化忧思录 四
四、洗钱工程
上世纪九十年代,内地县官为了向沿海经济看齐,掀起了兴办企业的热潮,用公库里的钱直接投资的“官办企业”和引进部分外资的“合资企业”在县乡两级政府所在地如雨后春笋,“工业化”似乎有一蹴而就之势。
“棉花书记”上任的明年,H县决定在县城南郊破土动工兴建一家制药厂,用于生产原料药“多种氨基酸”,命名为“H县氨基酸厂”。
十年前生产“多种氨基酸”制药厂除去土地出让金部分的建厂资金通常得千万元以上;可H县计划用于一期工程的建厂资金只有七百万元。
H县已有一家制药厂,是四年前前两任县委书记在位时兴建的,主要生产治疗呼吸道疾病的“蛇胆川贝液”,花了几百万元纳税人的钱,招收了两百多名工人,结果是斧头蛇尾,只勉强运转了两年就被迫停产。主要的管理人员长期闲在家里由财政发工资,工人则下岗失业。
新建的氨基酸厂按理应该在已经停产的原制药厂基础上改造扩建,这样不但可以节省至少三分之一以上的建厂资金,还可节省本来已经很紧张的城镇建设用地,让失业工人重新上岗;H县还可消除一桩影响很不好的“烂尾工程”。
可“棉花书记”没有作如是想,他是一个在花钱搞“建设”上有“大气魄”的人,要干就不能“废旧利用”,而是“重新再来”。
工程奠基后,“棉花书记”任命一个破产乡镇企业的一把手帅经理出任氨基酸厂厂长,全权负责氨基酸厂的筹建工程。
帅经理领导的那个乡镇企业是乡办企业,专门生产制药机械,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曾经生意红火,业务蒸蒸日上。他上任后才两年时间就把那个企业历年的经营成果挥霍一空,在欠下一屁股需要用纳税人的钱偿还的债务且卖光主要设备后关门停业。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经营外行,玩乐内行”,对女人、美酒和麻将的兴趣远远大于对自己职责的兴趣。药械厂职工背地里给他取了个绰号——“玩了死经理”。
“玩了死经理”因何被“棉花书记”选中为“H县氨基酸厂”的厂长,对外宣称的理由是帅经理曾领导过远近闻名的药械厂,有很丰富的药厂管理经验……其实药械厂与制药厂是两个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企业,一个属化工原料;一个属机械工程。
H县的小道消息则是另外的流言蜚语:“玩了死经理”和“棉花书记”是铁杆哥们,两人经常坐一辆小车晚上去省城“交流工作经验”。
氨基酸厂的建设进展得很快,不到一年时间一期工程就已验收达标,建起了一栋厂房和一栋办公楼,外加药厂周边的砖砌围墙,上报造价七百万人民币。可内行人说那三样水泥建筑最多也就值两百万元。
下一步的工作是招工和试制氨基酸样品,试制经费由公库提供。等到样品验收合格后再投资第二期工程。
“玩了死经理”在招工上有绝招,不问学历技术,也不管工作需要,只在乎对方的“财力”和“长相”。男人只要出得起高达五千元的“进厂费”;女人除了进厂费外还必须年轻漂亮就可“跳农门进厂”。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在本地“跳农门”对农民子女来说仍是一个有很大诱惑力的前景。
试制样品阶段按理只需要招收十来名有药学专业知识的技术工人就成,可“玩了死经理”一下子就招收了两多百名,其中只有一个药学中专生有点药学专业知识。
样品没有试制成功,就拿不到生产批文。药品不同于普通商品,拿不到批准文号的产品就不能上市。“H县氨基酸厂”的样品还没进入试制阶段,就一下子来了两百多名工人,其中的百分之九十五自然没有事作。于是“玩了死经理”叫多余的员工回家听通知,在家时间的工资照发,等氨基酸厂投产赚钱后再去财会室领钱。
氨基酸厂其余几位管理人员暗中抱怨帅经理在瞎胡闹,可“玩了死经理”一点不认为自己在瞎胡闹,他瞅着那近一百万“进厂费”,内心深处的那个欢喜劲是“局外人”不可能理解的。
原计划样品试制阶段为十天,可连续半年时间仍在继续“试制”,不但试制出的样品没一批合格,连试制样品用的“去离子水”也从未合格过。因为没有哪个员工知道怎么处理制备“去离子水”的“阴阳树脂”。没有合格的去离子水,怎么可能制造出合格的样品?
奇怪的是,如此简单的技术问题,在H县完全能够聘到解决此问题的技术人员,可“玩了死经理”从未想到要去聘请药学专业人士,任凭那几个门外汉在那里周而复始地“摸石头过河”。
整整一年过去了,“H县氨基酸厂”的样品仍在试制,两百多名工人仍旧在家“待业”,交了五千元进厂费,可没领到一分钱的工资,就是脾气再好的人忍耐也达到极限。他们纷纷前往氨基酸厂找“玩了死经理”讨说法,要厂方发放“拖欠工资”或退还交纳的五千元进厂费。“玩了死经理”的对策首先是“拖”,向前来要钱的职工发誓说要不了多久工厂就会投产,下欠的工资到时一次性补发;实在拖不下去就“赖”,说那些进厂费全用于建厂了,现在一分钱也没有,再说工厂不是他私人的,要钱别找他要,找县委县政府去;赖不掉就“躲”,从此根本不在工厂照面。部分熟悉他的员工找到他的家,可邻居说他家的防盗门好长时间没有打开过……
于是部分胆大点的“职工”找到县委县政府,可接待的人说此事县委县政府管不了,氨基酸厂的法人代表是帅经理,要找也只能找他去,县委县政府又没收他们一分钱的“进厂费”。
最后除了部分扬言要和帅经理“玩命”的椤头青要回了五千元“进厂费”外,大多数工人的进厂费依旧处于没有期限的“赊欠”状态,时间一长就不了了之。
H县氨基酸厂从建厂那天起直到今天一直没有正式投产过,但那个机构却存在了相当长一段时间。起初“棉花书记”指令H县卷烟厂去氨基酸新建厂房生产香烟过滤嘴,利润用于支付氨基酸厂管理人员的工资和“办公费用”;同时也可部分消除新厂房长期闲置造成的舆论影响。等到人们逐渐淡忘氨基酸厂的闹剧时,过滤嘴又搬回到卷烟厂生产。大部分管理人员重新安置,但氨基酸厂这个机构并没撤销,“玩了死经理”依旧是名义上的厂长,每年县财政拿出一笔预算用于支付他的工资和“办公经费”,直到前两年这块土地连同土地上的厂房被一家外资企业收购,“玩了死经理”作为“股东”(国有资产股依旧由他作代理人)进入企业高层管理层时,H县财政才停止对氨基酸厂拨款。
当氨基酸厂还没投产就无限期关门停业时,H县的人民终于了解到这项投资本身就是瞎胡闹,因为那时本市有几家氨基酸厂,在市场上供过于求,加上同行业的恶性竞争,近几年大都处于不同程度的亏损状态。H县这时挤进去凑热闹,就算能正式投产也是亏本赔钱?
人们不禁要问:一个堂堂的县委书记,花钱为何如此糊涂盲目,如此大规模的投资工程为何事先不进行市场调查,不进行认真科学的可行性论证呢?人人都知道帅经理是除了挥金如土吃喝嫖赌外什么也不会干的败家子,金山在他手里也会一夜间变成粪土,县委书记为何要单挑他来挑此大梁呢?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得以向一位从县级行政要位上退下来的“老干”提出了这个疑问,他的回答听来如雷轰顶。
“他比谁都清楚氨基酸厂不可能办起来,就算办起来也不能赚钱,平民百姓也许对氨基酸厂还有一线希望,他则从一开始就不抱任何幻想。”
“ 那他为何还要坚持办氨基酸厂?这不是醒着尿床吗?”听了老干的话,我一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他办厂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洗钱’”
“什么叫‘洗钱’?”
“你连这个都不明白?‘洗钱’就是把非法收入变成合法的。黑社会靠绑架抢劫弄来的钱要‘洗’一下才能变成合法资产,并因此申办赢利少或根本不能赢利的‘洗钱企业’。贪官要想把公款变成自己的钱,不能直截了当地把帐上的公款攫为己有,也必须通过某种方式事先‘洗’一下,最行之有效的途径就是办实业‘洗公款’。”
“你能把‘洗公款’说明白点吗?”
“我还是就事论事来现身说法吧,拿你所熟知的氨基酸厂来说事更容易理解一些。比方说那年某个能够决定政策的县长盯上了公库里的七百万元(纳税人的钱或出卖国有资产如土地所得),他不能把这七百万公款直接揣进自己的口袋,那是明明白白的贪污,会丢官坐大牢。他得设法把这笔公款‘洗’一下变成自己的。于是他想到了办厂,帐户上投资七百万,实际只投资两百万,其余五百万制造假帐‘洗出来’。作为‘洗钱’代理人的厂长自己贪污两百万,孝敬“恩主县长”两百万,剩下的一百万用来堵知情权力人物的嘴……”
“这种洗钱方式会造成多大的浪费!为了贪污两百万,竟然丢掉七百万公款?其中的两百万还完全浪费掉了,天底下竟有这等丧心病狂的事?”
“贪官只要自己能捞到两百万,浪费了多少公款他们才不在乎?公款经他们‘洗’过后自然会大大缩水。那个氨基酸厂其实就是‘洗钱工厂’,贪官筹建‘洗钱工厂’得选好两个要素:首先是投资项目,最好是必要总投资额大于计划投资额的项目,这样在工程半途而废之后就可借‘投资额不够’把责任推脱得一干二净。其次是‘洗钱代理人’,这个人的必备要素是大胆,还要肯背黑锅,名声也不怎么好,这就是为什么选帅经理这种‘玩字号人物’当厂长的内在原因。如果让你这样有良知和责任心的人来当厂长,氨基酸厂也许会办起来且运转赢利,可那位县长能得到什么?”
“…………”
我不否认这位退职“老干”因为大权旁落形成的“失落感”,因为心理不平衡才对在职县官有诸多不满,但仔细一想他反映的现象并非完全是情绪化的胡言乱语。H县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有不少官办企业,几乎每年都有一家新企业奠基筹建,投资过五百万的企业也不是一两家;可这些企业绝大多数都没有正常运转,要么象氨基酸厂一样还没开业就关门大吉;要么开业后闹腾一两年就人去楼空。勉强支撑到今天的一两家“脸面企业”则陷入严重的亏损,每年要靠财政补贴大笔钱才能让前来参观视察的上级领导看到一点“工业化”的迹象。
这些亏损企业、烂层企业也许绝大多数是基于县官的决策失误。县官的主观愿望是好的,是为了发展地方经济,只是因为缺乏经济知识,在决策时过于草率才吃力不讨好;但也有少数县官的原始动机就是为了“洗公款”,为了鲸吞公款才筹办“洗钱工程”——“往黑水河里投钱”。
“洗钱工程”除了氨基酸厂那样的官办企业外;还有官商合资企业。企业资本一部分来自县乡两级政府;一部分来自“外资”。这些所谓“外资”并不是什么外国资本,而是从这个县以外的中国其他地方引进来的。在H县的大部分“合资企业”中,引进的“外资”并不是什么人民币,而是生产设备。这些设备要么已经淘汰一文不值或即将淘汰值不了几个小钱,可帐上折合的资本额常常是几百万!本地政府投入的配套资金则是几百万实实在在的人民币!绝大多数县官也许是被属于中国公民的“外商”骗了;但也有少数县官对“外商”的把戏了如指掌,可仍坚持在“外商”不提供对等配套流动资金的情况下与对方合作,背后的内幕相信各位能够想象得到,一个“精明”的县官“外商”是绝不会亏待他的。这种情况属于贪官与“外商”合谋“洗”本地的“公款”。
中国步入二十一世纪后,政府投资日益规范化,县级政府直接投资办企业的现象得到了一定程度遏制,县官不能再随心所欲地开办“洗钱工厂”了。但另一种形式的“洗钱工程”又在县乡两级政府浮出水面,并且主要是“洗国家的钱”。
本届中国政府是对农民最仁慈的政府,农民种地不但不上交一分钱,每年国家还要拔出大笔款项来支援“三农”,仅“退耕还林”和“转移支付”两项每年就得耗费上百亿人民币。中央政府如此亲民爱民,作为百姓父母官的县官们应该更进一步,充分发挥职务活力,大力压缩公务开支,提供配套资金来支援三农。很多县官也许这样做了,但更多的县官不但没有与中央的“服务三农”政策接轨,相反还盯上了国家下拔的“支农专款”,尤其是“退耕还林”款,为了把这笔钱“洗”进自己的口袋不择手段。
还是拿H县来说事吧!
H县F乡有一片茶林,几十年来一直是所在村的经济支柱产业。F乡为了套取国家的“退耕还林”款,把茶树全砍了,连带茶林外围的几十亩杉树也遭了殃,然后在空出来的土地上栽种白果树,于是就成了“耕地返森林”工程了,于是国家就拔来一大笔钱。整个工程耗费也许不到十万元,可帐上的工程款却高达七十多万,多余的钱去了哪里各位自然心知肚明。
白果树栽上后,套取国家“退耕还林”款的目的达到了,相关人物的腰包也鼓起来了,于是就万事大吉了,随后的管理也就没必要认真了。结果不到半年,三分之二的白果树苗在山上“消失”了,部分是自然死亡的,部分是被当地人拔走的。两年过后,当地政府又以区区四千元的代价把这座茶山卖给了一位“承包人”。此人把没有任何成林希望的残存白果树苗全部铲除,然后全栽上五年就可成材的白杨树……
国家的七十万“支农专款”就这样在两年内“洗”成了四千元,另外还赔上一座年产值几十万元的茶山和杉树林!
部分县官乡官们“洗”钱的手段真的太“狠”的!他们“洗”掉的是中央政府亲民爱民的“赤子之心”啊!
…………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