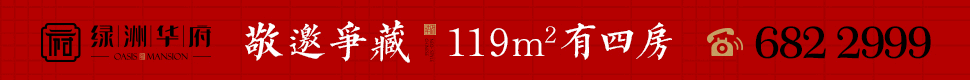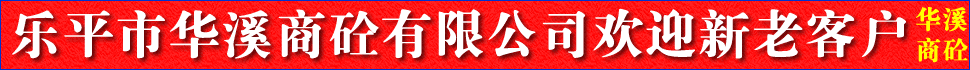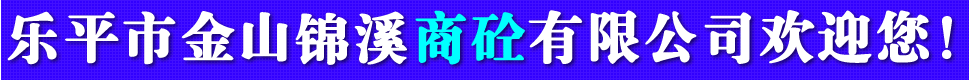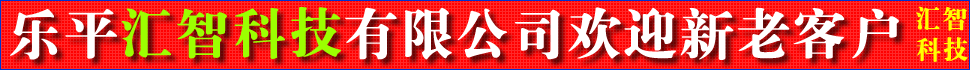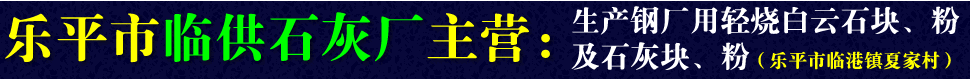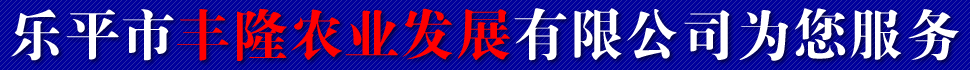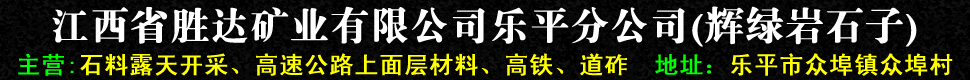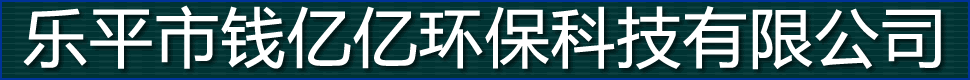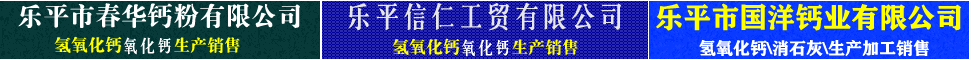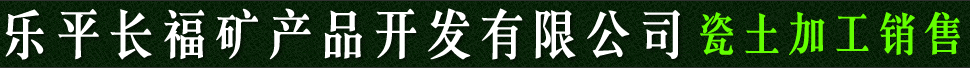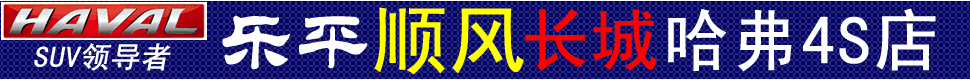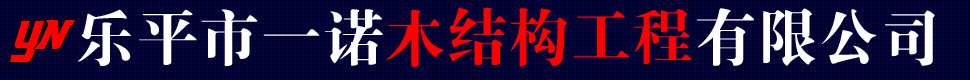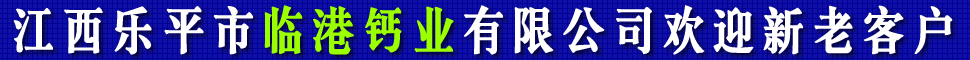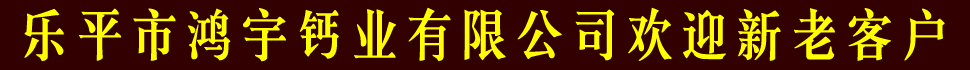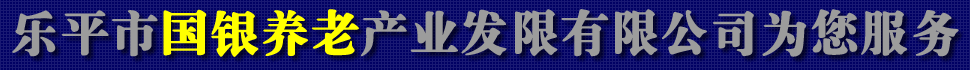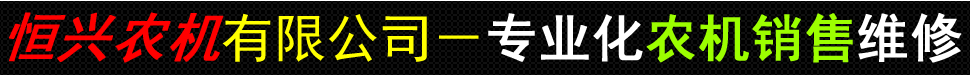新闻内容
我的千面女郎
——兼读岱森先生的<<普罗米修斯的赐福>>
人为什么活,该怎样活,活过之后将如何,这些回复生命本源,追踪幸福的本质的问题是困绕人们生存状态的大问题。没有大明智和豁达的幸福观的人们注定得在生与死,终极与虚无之间艰难跋涉。
正如臧克家先生所言,“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选择不同的生活态度和不一样的幸福观,其一生得到的生死结果也许就迥然不同。伟大导师毛泽东教导我们,“人固有一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对死的方式的选择本身也是对生之过程的一个遴选。都说雁过无声,人活一世,大多数人追求的理想状态其实很简单,不求流芳千古,至少不至于遗臭万年吧。佛家也好,道教也罢,无一不教诲人们克服苦难,顺应苦难,注重德与行的修为。”生如夏花之绚丽,死如秋叶之静美”,有着数千年儒家思想发展土壤的华夏大地培育了独特的生死观和幸福观。作为一种最高的生存境界,从马斯诺的需要层次理论上来说,在满足了生存欲望后,人们为了追求自我实现的最终目标,始终孜孜以求。在朝这一目标奋进的同时,内心与理想连接,梦境与现实等高,此时的人们即使被汗水浇灌,毕露蓝缕浑身还是有使不完的力。这个过程是老农期待丰收的过程,是十月怀胎等待分娩的母亲的幸福。
精神与物质哪一个对我们生之幸福至关重要,我想不同的情境之下得出的答案完全不同。现实中有的人物质上相对富足,然而整天浑浑噩噩,度日如年;有的人物质上相对匮乏些,但精神充盈。由此我想到一些乞丐,如果他们不是头脑不清醒,或是智力有障碍,他们整日的悠闲与从容,绝对是我们艳羡的精神富翁。话说回来了,也许正是他们的那种生理重创才换来了他们一世的清爽。板桥先生所言甚是,“难得糊涂”,在没有功利和物质的羁绊下人们又何尝喜欢逐鹿中原,决战沙场?
幸福的感觉足以让人回味良多。古语言人之大幸莫过于“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一个“时”字恰如其分地表述出了幸福只在当下,是一个稍不经意就从我们指间滑过的玩偶。普罗米修斯最初的赐福是未经雕琢的幸福的胚胎与轮廓,人类因了有思考的情趣,有经历苦痛时的心酸才有了对幸福的品读。也许眼下一切的梦境与恍惚,甚至境地不佳只是不远时幸福的一种表象与预兆,因为大喜往往与大悲同病相连,一衣带水。人们确实应该明白上帝对幸福赏赐的理度,于大悲大喜中读懂幸福的个中滋味,永不抱怨。面对无穷期的等待,焦灼的困苦,抑或有生之年也可能无法兑现的幸福遥想,我们都得抱一颗与之相吻合的心态去品味。幸福本身就是一种抽象的,无法度量的感觉,是一张不可能始终攥在手心的“入场券”。它期待着我们在心灵播洒它的种,植下它的根,让这种感觉始终如一,永不凋谢。
幸福说到底就是一种与精神等高的极致。没有任何人可以给幸福下一个指标,给一个系数,因为幸福总是以快乐与阵痛,等待与遥想交织的形式出现,用最简约的一句话定义也许就是“痛并快乐着”。不同的人生境遇有不同的幸福观,不同的人生态度产生不同的幸福感觉,幸福如千面女郎让我们感叹生命的缤纷色彩与万方仪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