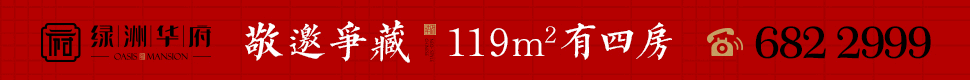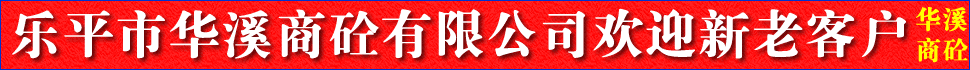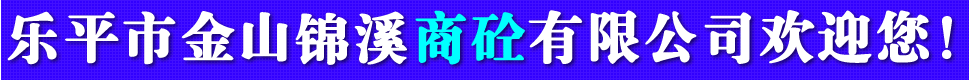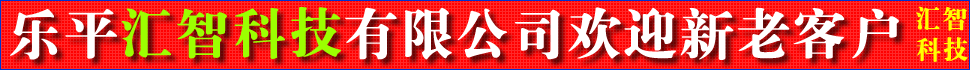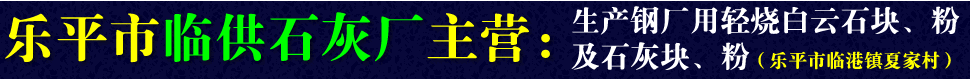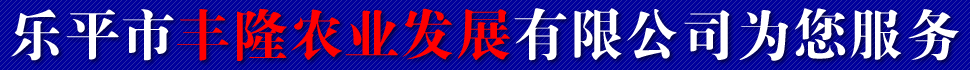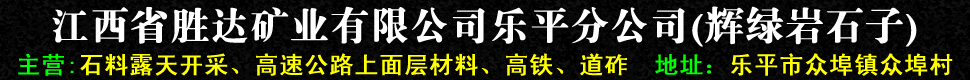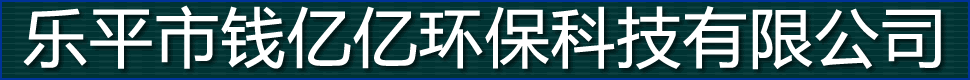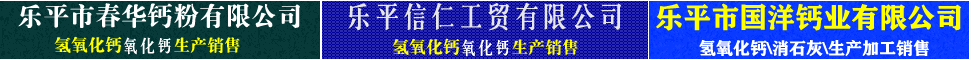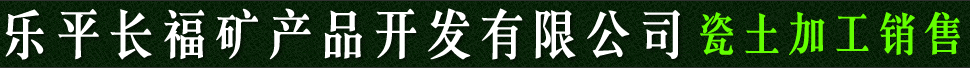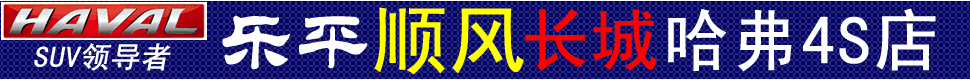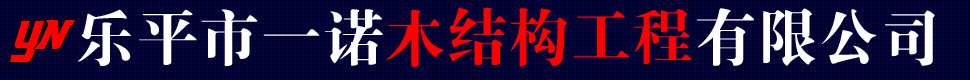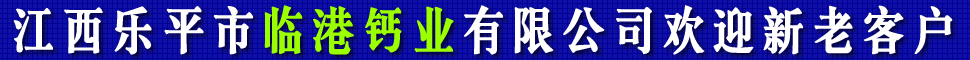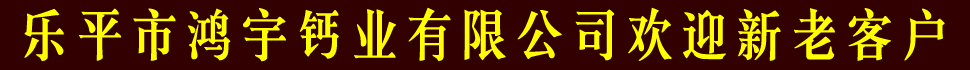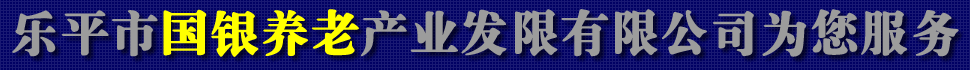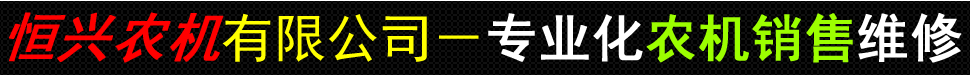新闻内容
范晓波:无涯
你外婆说得好,人都是在世上作客。每逢听闻相熟的人离世,母亲总叹着气这样说。
母亲认为外婆的话朴素而形象,我也深以为然。住几天、几年是作客,住八十年、一百年也是作客,谁都不可能一直留在世上。只是人从哪里来到世上?作完客又回到了哪里?外婆没说,我和母亲也没讨论过。
这问题全世界的哲学家琢磨了两三千年也没找到令人信服的答案。普通人就懒得费那个劲了。
母亲重病后,特别是第二次手术失败之后,我常找时机跟她探讨这个话题。我的理解是,既然在世上是作客,那么,作客的过程就不是常态,起点和终点才是常态。作客的待遇有许多种:被敬若上宾;被冷落、打击;被不冷不热地应付;或者,一波三折、五味杂陈……被打击自然无意久留,待遇再好久了也会麻木、疲惫,只有回到家里,身心才会彻底放松。
这信念源自外婆的启发,也得益于宗教的帮助。
那几年我临时抱的不仅是佛脚,基督的脚也没少抱,书没少翻,寺庙和教堂没少跑,省内和省外的,只要有机会就一定拜谒。向法师求教,听信徒唱诗。有时还请学佛颇有感悟的居士来家里传经送宝。
我努力让母亲建立某种我自己都来不及确认的信仰。
与当初致力于让她相信病一定能治好不同,这是绝望之后的努力,无望之后的希望,但是,未必不是希望。
大多数时间,母亲听得心不在焉。她虚弱地仰靠在沙发上,耳朵接受着我的絮叨,眼神却飘忽地望着窗外植物的碧绿身影。对她而言,香樟鲜嫩如花的新叶和紫藤花张灯结彩的身姿可能是种更实际的鼓励与心理暗示。
她曾是高三政治课把关老师,还教过多年初中物理,虽觉得外婆的比喻有道理,却很难沿这条思路推演下去,她被从小所接受的物理和哲学常识拦在半路上。也就是说,无法倒空自己。
她将信将疑,每一轮思想搏斗中,怀疑总是比相信的次数多一次。她只是不用语言抵触我,她微笑着珍惜我的善意所蕴含的温暖。
我也经历过这阶段,被一些科学常识所束缚,无法相信未经验证的东西,更无法接受佛教所描绘的六道轮回、基督教所说的天堂与地狱。宗教对这些经验之外的世界不仅言之凿凿,而且过于具象,确实很难让人采信。
但是,在一些具体的教义中,宗教对生命现象的论述又同科学实验的结论高度吻合,比如佛教认为生命是种“不生不灭”、“不增不减”的存在,这同物质不灭的科学定律是那么一致。而且,千年前的佛教典籍就告诉我们一滴水有万千生命,显微镜发明出来后,果然能看到一滴水里有万千微生物。
我也不断意识到我们所信赖的常识的粗浅,很小的时候我怎么也想不通宇宙没有边际,一直朝一个方向飞总有到头的时候吧?长大了才知道,要理解宇宙必须在三维空间的常识上加入时间的维度。
人类的科学常识本身也是在不断自我推翻和超越的。
促使我彻底放弃成见的是一个有意思的发现,牛顿、爱因斯坦等许多大科学家最后都皈依了宗教。他们是不是发现自己穷极一生探寻的谜底宗教里早有明示或暗示呢?
宗教有没有可能是更高等的智慧生物送给人类的礼物?地球上许多古老的文化遗址里都能找到现代科技的蛛丝马迹,宗教是不是也是如此呢?
我跟母亲说,我也理解不了六道轮回,但我相信生命确实不存在生与死的差别。生死只是生命的两种不同形式,就好比无线电波,它一直在空中存在着,我们打开电台时它被我们听到,关掉电台就听不见,但我们不能说,我们听到时它是活的,我们听不见时它是死的。
母亲也认同我的一些分析,但最终也没有被我摆渡到岸。可能,病痛对于她是种更具体可感的存在,干扰着她建立新的生命信仰。
她的不甘与不舍成为我心里永久的伤痛。
我迄今为止也没笃信哪门宗教,但我在对多门宗教的敬仰和观察中学会了一种思维方式:任何常识,都可能是一种局限性极大的真理;而许多真理,未必可以马上用常识去验证。
去看一个生病的朋友。
从医学常识看,由于发现得早,她的病应该还不会危及生命。不过她还是谈到了恐惧。她这样解释为什么办了住院手续人却住在家里:住在医院里,看见形形色色的死亡,心里的压力会特别大。
这个我很理解。医院有时是治人的地方,有时是害人的地方。医院最令人不满的地方在于,它查证恶疾的次数远多于治愈恶疾的次数,剥夺尊严的能力远大于挽救尊严的能力。
有两年时间我不断陪母亲出入各大医院的重症病房,之后看谁都像有暗疾在身而不自知的人,也经常莫名其妙地怀疑自己其实很健康的身体。
朋友说,以前死是个特别远特别概念化的字,谈起来很轻松,现在它贴着自己的脸呼吸了,还是会特别恐惧的。
这点我不完全能理解。这位朋友是半个哲学家,素来因对世事的超然姿态被大家激赏
在我看来,她是人群中活得特别清醒特别通透的那类人。
她怎么也会觉得死亡是种可怕的状态呢?
她说可能是因为未知吧。
既然未知,为什么不从乐观的角度设想,也许所谓的死亡是种比活着更好的状态呢?我觉得这恐惧还是常识造成的,常识告诉我们,活着才能享受阳光、蓝天、四季,所以要珍惜;常识告诉我们生命只有一次,所以特别宝贵;常识告诉我们死亡是件不好的事,所以亲友离去我们一定要悲伤。
有个问题,人类的所谓常识,在宇宙面前,低幼得可以忽略不计,人类的文明才还不到一万年历史,在地球的45亿岁的年龄面前只是一瞬,地球在宇宙中又渺小如尘埃。一种一万年都不到的文明对宇宙规律的解读该会有多么幼稚呢?肯定比一只蚂蚁对人类的理解还肤浅一万倍。
前不久看到一个资料,有科学家依据种种迹象得出结论:地球是外星生命囚禁人类的监狱,因为人类的文明太原始太野蛮,所以用地心引力把人类囚禁在地球上。还有更惊世骇俗的观点,宇宙大爆炸是人为的,也就是说,宇宙也是被有意制造出来的。是谁创造了宇宙?难道,真有个类似于上帝的东西存在?
这些观点猛一听都很荒谬,不过回想一下,仅仅四百多年前,当有人宣称地球不是宇宙中心时,还被自以为真理在握的人处以火刑。那么,又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
不知是被我滔滔不绝的热情感动,还是被语言的洪流冲断了思绪,朋友似乎默认了我的歪理,望着在厨房忙碌的爱人说:人对死亡的恐惧,还有个很大的原因是牵挂,舍不得离开亲人、爱人。
我说,情感牵挂当然是痛苦的,不过我们也可以换一个角度想,假如生命有多个时空的存在形式,那么,作客回家后,就可能和另一些亲人团聚,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之类,他们同样是你至亲至爱的人,他们已经等你很久了。这样一想,两种牵挂的痛苦是否可以相互抵消呢?
她笑着对我的想法表示惊讶,问:你真是这么想的?
我真是这么想我的。至少近几年如此。
不仅和这位朋友,跟其他朋友我也阐述过这些心得,并持续地在心里强化它,让它逐渐沉淀为精神养分,一点一滴渗入日常生活的裂隙。
我不看网上那些哭哭啼啼的诀别新闻,不参加过度渲染悲情气氛的追悼会,两千多年前的庄子尚能做到用击盆而歌的方式送别妻子,以高科技、高智商自诩的现代人在这方面总不能一点进步都没有吧。
我也越来越反感耸人听闻的健康科普和医疗广告,“如果你有某某症状,就表示大病来临……如果你不怎样怎样,就会怎样怎样。”这种粗暴的标题党每天变换模样占据着各大媒体的健康专栏,究竟是要挽救健康呢,还是破坏心理健康?我觉得一个真正文明的社会不应鼓吹对死亡的偏见,更不应利用人们的恐惧心理盈利。
每年一些特定和不特定的日子,我会去母亲的墓前看看。如果天气好,多半还会在那里歇歇,坐坐。
墓地是我帮母亲选的。母亲生病前就多次提出要先置好墓地,她考虑的因素是墓地在飞速涨价,早买可以替子女省很多钱;也怕城后的公墓满员后要迁到远郊,我们扫墓不方便。父亲觉得这事不吉利一直不肯办。她离世前的一个星期,我悄悄去城后的公共墓地帮她选了依山面湖的一块风水宝地,很适宜远眺,也考虑了情感因素,正前方的韭菜湖边,是母亲少年时住过的洗麻厂。
深秋的时候,墓地上阳光白亮煦暖,有一种恒定的安静气氛,与城区的争斗、吵闹以及与之相关的悲欢情绪形成对照。坐在那里,许多与活着相关的心理波动都显得失真和过于隆重。我忽然想到一句话:墓碑般的镇静。
平常遇上忧心与恐惧的事,我也常记起这句话。我想,我们所有的担忧与慌乱,全都因为在世事中陷得太深太痴,把购物而非观光看成旅行的意义,把短暂的瓜葛看作永恒的牵绊。如果具备了墓碑般的冷静与镇静,还有什么能晃动一个人的心志并将他打败呢?
外婆的话也我一直记着,既然在这个时空是作客,既然还没到有人唤归的时刻,那么,不妨从容一点,宽容一点,自尊一点,自爱一点,像个有礼貌有风度的客人,乘兴而来,兴尽而归。
2015年第6期《散文》